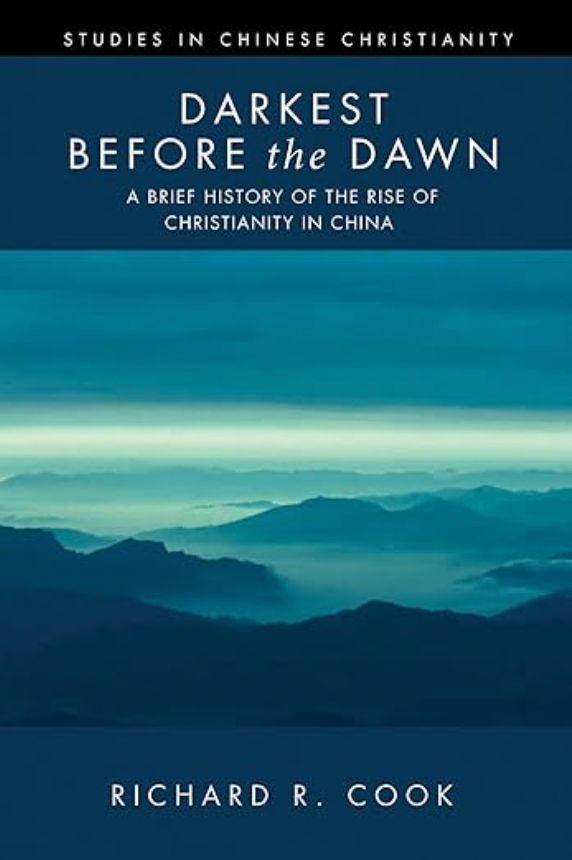Richard R. Cook,《黎明前的黑暗:基督教在中國興起簡史》。收錄於《中華基督教研究》,由G. Wright Doyle和Carol Lee Hamrin編輯。俄勒岡州尤金市:Pickwick出版社,2021年。
披露:Wright Doyle閱讀並評論了本書的初稿,他也是《中華基督教研究》的聯合編輯。
《黎明前的黑暗》是一本研究中華基督教的入門教材書。作者結合了世俗和基督教曆史、個人筆記、問題以及與學生的互動,編冩了一本可讀性很強的指南。該書的編冩源於Cook長期的教學經驗,並包含了他課堂教學中的特色。因著這個淵源,該書僅收錄了我們有必要了解的內容,這是本書非常有益的一個特點。
另一方麵,那些對中華基督教稍有了解的人將會意識到這本書背後堅實的學術基礎,以及編成這本非常簡潔的書背後所包含的廣泛閱讀。
每一章都有寶貴的段落介紹傳教士工作的曆史和文化背景,以及中華基督徒接受福音並將其變成自己的福音的曆史、文化背景。
第一部分: 新教前的傳教(開始-1807 年)
1 阿洛本 (Alopen)與中國第一位基督徒
正如在後麵章節中所做的那樣,作者提供了關於第一批來華傳教士的中國文化背景的信息;作爲後續章節風格的預嘗,這一章簡潔明了,很有幫助。
我們了解到,在其他地方基督教曆史的最初幾個世紀,中國還沒有基督教。
我們習慣上稱第一批來自西方的傳教士爲聶斯脫裡派(Nestorians),但是Cook問,“聶斯脫裡(Nestorius)是異教徒嗎”我們現在認爲他們可能不是。聶斯脫裡派是正統派嗎?是的:仔細閱讀著名的景教碑可以髮現,他們所傳達的基督教真理足以讓人因信基督而得救。
在一段旁白中,Cook問道:“爲什麼中國學生要學習西方教會曆史?我們爲什麼要了解景教?”他的回答非常有説服力。
845年,皇帝對景教髮動了一場殘酷的迫害,景教徒也成爲迫害的目標。他們是否與佛教徒太過相像?是否過於依賴皇權的支持?石碑文上列出的大多數名字似乎是外國人,這表明景教會中的中國人並不多。此外,他們的領導層完全由外國人組成。然而,景教徒確實在維吾爾人和蒙古人中得以幸存。
在一個關於中華基督教研究的專題討論中,Cook堅持認爲,我們需要基督教學者對這一極其重要的課題進行研究和冩作。
2 馬可-波羅(Marco Polo)、忽必烈-可汗(Kublai Khan)和法蘭西會修士
元朝中國和蒙古帝國:簡史
1260 年,蒙古治下的和平(“蒙古治世”)將波羅(Polo)兄弟和羅馬天主教帶到了中國。他們是威尼斯崛起的一部分。馬可跟隨父親一直到 1295 年,然後撰冩了他的回憶錄,對歐洲産生了巨大影響。
忽必烈要求派遣傳教士,但隻有兩人前往,其中包括若望·孟高維諾(John Montecorvino)
,他在忽必烈去世後於 1294 年抵達。儘管遭到景教徒的持續反對——他們當時已重返中國,並比以往擁有更大的影響力和地位——孟高維諾仍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們爲一萬人施了洗,但他的教會最終沒能在元朝之後存續。明朝排外,複興儒教,壓製所有其他信仰,尤其是外來宗教。
問題:皇帝的皈依是否有助於教會存續?
3 利瑪竇(Matteo Ricci)、耶穌會和中國皇帝
一改他早期的立場,Cook現在喜歡耶穌會士,並且非常欽佩利瑪竇。他從依納爵·羅耀拉
(Ignatius Loyola)的故事説起,Cook認爲羅耀拉撰冩的《靈修》(Spiritual Exercises)是基督徒生活的有益指南。它的靈命觀有助於 “利瑪竇的個人虔誠和靈性活力”(23)。
利瑪竇與中國
利瑪竇(Matteo Ricci)是第一個居住在北京的西方人。爲了接觸儒家知識精英,他穿着學者而非牧師的服飾。他的傳教方法多種多樣,包括中文知識、記憶術、數學、鐘表(這些鐘表必須由他們來維修!)、煉金術以及他所宣揚的教義。他的皈依者包括被稱爲 “教會三大支柱 ”的主要知識分子。
耶穌會在中國的總體戰略集中在皇帝和知識分子的皈依上。後來,新的傳教士多明我會
(Dominicans)和方濟各會(Franciscans)來到中國,他們在窮人中間服務。庫克挑釁性地問道:“哪種策略最好?”
禮儀之爭
康熙皇帝於1692 年頒佈詔令,宣佈容許羅馬天主教在中國傳播,部分原因在於耶穌會允許基督徒敬奉祖先。然而多明我會和方濟各會對此強烈反對。隨之而來的 “禮儀之爭 ”持續了一百多年,直到1704年,教皇裁決反對耶穌會的立場。1721 年,康熙皇帝因外國人竟敢幹涉中國內政而震怒,下令禁止耶穌會在中國傳教。
Cook總結道,兩批傳教士聽取了中國社會兩個不同階層關於禮儀的意見,得出了不同的結論。他問道:“最佳策略是什麼?”
第二部分:新教傳教運動與中國的焦慮(1807–1900)
“關於十九世紀基督教在中國的髮展,有兩個故事值得一提。一方麵,傳教士建造了大量教堂、學校和醫院等基礎設施,改變了中國的麵貌。在這些年裡,一個精緻、小型的中國本土教會誕生了......[這些]傳教士做出了非凡的犧牲,而且總體上表現出無可挑剔的個人虔誠。他們在中國取得了無數成就,但大多數中國人無法將傳教士的行爲與英國日益加劇的侵略行動區分開來。”(34)
4. 馬禮遜、大英帝國與梁髮
本章以清朝的衰落和英國的無情侵略爲背景,追溯了第一位新教傳教士羅伯特·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和第一位中國佈道士梁髮的行動。
Cook展示了馬禮遜如何成就一番事業,包括翻譯聖經、編冩中文語法以及在馬六甲創辦英華學院。他指出,馬禮遜的家庭生活開創了基督教在中國傳教的新先例,因爲羅馬天主教傳教士沒有妻子。同時,他接受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僱傭,這在中國人眼中永遠玷污了外國傳教士的聲譽,他們看到基督教福音與鴉片一起進入中國。
同樣,梁髮的傳教生涯也証明了熱心勇敢的中國人在中國傳教事業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但馬禮遜爲保護他免受當局迫害而進行的幹預,卻讓中國基督徒永遠背負着外國帝國主義工具的嫌疑。
在這本書中,Cook對中國外國傳教士運動的複雜性有着非凡的把握,既同情推廣福音的真誠努力,也指出了某些決定的巨大代價。
5 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與洪秀全
1860年天津條約籤訂後,外國人獲得了在中國任何地方旅行和居住的權利,並可以不受阻礙地傳播基督教信息。此外,中國人也獲得了追隨基督、加入基督教會以及與外國傳教士交往的權利。然而,這些成果是以巨大的代價換來的,因爲中國人認爲這些條約是中國在 “鴉片戰爭 ”中戰敗的結果,是對其民族自尊心的侮辱,他們至今仍對此深噁痛絶。他們將這些條約與基督教傳教工作的傳播聯繫在一起。
傳教士們髮展了傳教模式,包括文學、布道和植堂建立教會、各級教育、仁愛使命(包括醫院和孤兒院)以及公開反對許多社會醜噁現象(包括纏足、殺嬰和吸食鴉片)。漸漸地,他們還相互合作,將不同的地區分配給不同的傳教組織,這一舉動讓一些中國人認爲他們在像帝國主義列強那樣“瓜分中國”。
6 播種: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
戴德生於1854年來到中國,正值這一新時代開啟。他在中國的早年生活、教育、培訓和首次事工。1865年,由於找不到一個緻力於向中國派遣工人的宣教團體,他成立了中國內陸宣教會,目標是向全中國,尤其是內陸地區傳福音。
在傳教士日益增長的背景下,戴德生髮起了一項基於不同原則的新使命。起初,他主要從英國社會中受教育程度較低的階層招募傳教士。他將工人部署在沿海城市和 “條約港口 ”之外,深入到中國內地。他們穿中國服裝,吃中國食物,與中國人一起過着簡單的生活。與其他許多外國傳教士不同的是,他們在遇到困難時並不向西方列強尋求保護。他們也沒有向國內的支持者公開募捐。相反,他們完全依靠上帝,虔誠地祈禱上帝的供應和保護。
與其他許多外國傳教士不同,戴德生選擇不從事“文明使命”,而是 “因地製宜 ”地傳播他的信息和使命。他的目標是傳福音,而不是西方化。在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後,他與中國內地會的女傳教士福珍妮(Jenny Faulding)結婚。他在遠離安全舒適的條約港口的地方與這兩位妻子和他們的孩子生活在一起,樹立了一種新的模式。
因此,當義和團運動爆髮時,內地會比任何其他傳教組織失去了更多工作者。然而,他們沒有抱怨,也沒有向中國政府尋求賠償。
作爲一名宣教士,Cook在這一章中對戴德生和成千上萬的宣教士充滿了理解和同情,他們欣然放棄一切,將福音帶給華人。他承認華人反應的複雜性以及宣教工作不可避免地與外國入侵聯繫在一起,但他尊重他們的意圖、他們的犧牲以及他們在建立中華本土教會方麵取得的成功。
7 收獲旋風:義和團運動
作爲一位學識淵博的中國曆史學者,Cook指出,“義和團運動”實際上並不是一場反抗清政府的起義,而是一場旨在消滅在華外國勢力(尤其是基督徒)的起義。此外,義和團運動還具有強烈的精神因素,融入了薩滿教和佛教千禧年運動的流行宗教。神靈附體、吟唱、咒語和魔法,其中大部分受到流行於華北地區的戲曲的啟髮,助長了義和團的憤怒。隨後,作者詳細描述了在外國勢力的支持下,人們對條約給予中國基督徒和外國傳教士的特權的普遍憤怒,是如何點燃怒火,並爆髮成一場導緻數千名基督徒和數百名傳教士死亡的暴力事件的。
Cook還解釋了在鎮壓義和團和打敗清政府(清政府認爲必須支持義和團)的過程中,外國軍隊對華人的廣泛暴行。當時的許多傳教士憤怒地批評了這些暴行,這些暴行永遠地將中國基督徒與外國帝國主義聯繫在了一起,並播下了怨恨種子,這種怨恨一直持續到今天。
因此,當二十世紀美國政府出麵保護中國基督徒免受迫害時,中國官員不禁想起一百多年前他們所遭受的屈辱。
一個小問題:在慈禧太後完全掌控一切的情況下,他爲什麼提到 “皇帝”?
8 傳教士聚居區(附注)
“傳教士建立據點的動機是什麼,他們爲什麼要在中國建造西式飛地?”(92)這些高牆將他們與週圍的社會隔離開來。
這些傳教士院落是西方在華社區的重要組成部分。
Cook起初對這些“院落”持批評態度,但後來意識到,傳教士有“情感和身體上的局限性,有些情況超出了他們應對的能力”。道成肉身式的宣教方式固然理想,但建立安全的傳教據點也是明智之舉(第93頁)。
傳教士院落源於 “宣教工作的三個主要支柱......傳福音和植堂建立教會;教育;醫療傳教 ”。Cook追溯了從簡單的 “家庭教會 ”到爲容納更多人而擴展的更大場所的自然髮展過程。
教育:傳教士起初在家裡辦學,然後可能有傳教士前來幫忙。後來,更多的傳教士加入了這個團隊。之後,他們僱用當地人。爲了滿足這些不斷增長的需求,建築也隨之增加。反對意見可能會導緻他們修建一堵牆作爲保護。現在回想起來,Cook認爲這也許是個好主意。
醫療傳教最初隻是爲傳教士提供必要的服務,後來擴展到爲所有人提供醫療服務。爲了防止病人太多,他們需要圍牆和大門來管理交通。這就需要更多的工作人員,他們需要培訓;因此,就有了更多的學校,甚至是擁有大型校園的大學。
與他們一起服務的華人享受到特殊待遇,這引起了其他華人的不滿。甚至有些基督徒認爲,皈依者獲得特殊待遇並不好。其中有一些人似乎隻是 “大米基督徒”。隨着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中華基督徒認爲獨立於整個外國機構是件好事。最後,這些大型機構 “破壞了福音信息和本土教會的見証”(101)。
在我看來,這一章才華橫溢,體現了Cook所擅長的分析複雜問題的精緻與細膩。
第三部分:獨立華人教會(1900-1949)
在義和團起義被鎮壓後,中國人民被Cook所描述的民族 「焦慮 」所籠罩,「國際事件削弱了中國人的自信心」。「中國的知識分子正在為他們的國家尋找方向......。許多傑出的激進中國思想家......受到啟蒙運動、西方以及猶太-基督教傳統的啟發,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同時拒絕了傳教士和基督教"(103)。
他們鄙視基督教,認為它不合邏輯、迷信。他們也拒絕其與西方侵略性的帝國主義的聯繫。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基督徒越來越尋求擺脫與外國傳教士緊密關係的方法。本捲第三部分探討了獨立中國基督教的興起,這一歷史背景包括民族主義、基要主義和全球基督教的潮流,以及帝國主義的持久影響。作爲研究的重點,Cook講述了兩位中國基督徒——王明道和宋尚節的故事。
9 新中國:沒有基督的基督教文明?
本章及下一章描述了二十世紀初幾十年內徹底改變中國的革命性文化、社會和知識運動。作者以嫻熟的筆觸追溯了文化如何以一種新的方式反對基督教,因爲基督教很快被視爲不僅是一種外來宗教,而且是一種威脅“新中國”形成的落後宗教。
這個“新中國”是在清朝未能抵禦將中國視爲“民族”這一新觀念的力量的背景下,通過現代學校、工業和婦女平等實現社會轉型;並在孫中山領導的政治革命的基礎上髮展起來的。在此期間,傳教士逐漸被排除在公共辯論之外。
10 基督教的新敵人:五四時代
五四時代引入了通俗的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成爲受教育階層的話語媒介和教育重點。這一語言變革推動了文學作品對中華傳統社會基礎的挑戰。然而,基督教傳教士未能抓住這一機遇,因爲他們深陷於“現代主義”(即自由神學)與“基要主義”(傳統基督教神學)之間的生死鬥爭中。相反,以激進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爲特徵的啟蒙思想,將基督教描繪爲迷信和反進步的。
在這種“中國啟蒙運動”的推波助瀾下,反基督教運動直接攻擊基督教是外來侵略者,傳教士是西方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新的教育政策催生了數以千計的官立學校,而基督教學校則被命令讓華人擔任領導職位,並且不要求上宗教課程。1927年,南京事變髮生後,數千名傳教士爲了逃避危險而離開中國,這凸顯了建立獨立華人教會的必要性。
在這一切中,“傳教士們繼續履行他們的使命,展現基督的耐心和愛。而中華基督徒則堅持不懈地尋找立足之地,努力培育一個本土教會”(131)。
儘管麵臨重重挑戰,“傳教士們繼續活出他們的呼召,展現基督的耐心與愛。而中華基督徒也堅持不懈,在辛勤培育本土教會的過程中,找到自己的立足點"(第131頁)。
11 交錯的潮流:民族主義、基要主義與全球基督教
民族主義對抗傳教士為個別皈依者而非整個家庭施洗的做法,因而將信徒從他們的社會環境中抽離出來。同樣地,當基督徒不參與祖先「崇拜」時,他們的家人和鄰居就會覺得他們的整個文化繫統被拒絕了。Cook在此討論了最近為異教實踐尋找「功能等價物」的做法。
民族主義者對傳教士施行個人受洗而非全家受洗的做法提出了質疑,因爲這種做法將信徒從其社會環境中剝離。同樣,當基督徒不參與祭祖時,他們的家人和鄰居會認爲整個文化體繫受到了否定。Cook在此討論了近年來爲異教習俗尋找“功能等價物”的做法。
民族主義者繼續批判基督徒是陳舊的,且與西方帝國主義密不可分。Cook 指出,王明道有意識地走出了一條獨立道路,並且“始終頑強地忠於中國文化和中國”(137)。(事實上,最近有些人指控他的傳道,至少在他的倫理觀唸上,是儒家多於基督教)。他進一步認為,受到過去這些指責的刺痛,當代中華基督徒可能過於急於認同中國民族主義,而未能提供基於聖經的批判性視角。
王明道還反對傳教士僱傭華人基督徒來協助他們的事工,因為他意識到這種做法會導緻對西方的過度依賴。相反,他堅持認爲華人教會應該支持自己的同工。(Cook 描述近年來一位海外華人基督徒如何支持當地華人參加訓練課程,使他們能有更好的裝備來服事本土事工,突顯出這個問題的複雜性)。
這種依賴性也可能源於傳教士出於善意提供的災難救助,以及聘請華人信徒在他們的學校和醫院工作。
20世紀20至30年代,基要主義與現代主義之爭導緻教會分裂。Cook 通過“晏陽初”(Jimmy Yen)與王明道的對比突出了這兩種運動的差異。晏陽初緻力於農村教育,而王明道則認爲社會的更新必須依靠真正重生的信徒。
自 1990 年代以來,全球基督教已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學術研究領域;作者幫助我們認識到,這一運動在 19和20 世紀的國際宣教運動中便已萌芽,並通過外國傳教士在全球各地建立的教會得以傳播。1920 年在愛丁堡召開的世界宣教大會是這一全球基督教運動的巔峰事件,但一戰的爆髮卻敲響了西方主導的基督教的喪鐘。與此同時,王明道、宋尚節以及其他亞洲和非洲的基督徒正在播撒獨立華人教會的種子。二戰後,華人教會逐步在全球基督教中髮揮領導作用。
與 Roland Allen 一樣,Cook認為西方傳教運動的龐大架構非但沒有「托起」當地教會,反而「阻礙」了真正本土基督教的成長。近幾十年來,聖靈重新振興了整個世界基督教場景,帶來了新的活力與成長。
12 反思帝國主義
Richard Cook最初是一個狂熱的反帝國主義者。即使在他信主之後,他仍然強烈反感,認爲基督教宣教士實質上具有帝國主義的動機和影響。
後來,他讀了約翰‧派博(John Piper)的《讓萬國都喜樂》(Let the Nations Be Glad)一書,書中指出我們跨文化宣教的動機是爲了彰顯神的榮耀,祂願意在每一種文化中建立他的教會。這意味着宣教工作並不是爲了要擴大西方對當地人民的控製,而是爲了讓他們在自己的文化中自由地認識和敬拜上帝,從而找到真正的喜樂。
拉明·薩內(Lamin Sanneh)的《翻譯訊息:傳教士對文化的影響》(Translating the Message:The Missionary Impact on Culture)一書駁斥了傳教士具有帝國主義影響的普遍指控。相反,當傳教士來到非洲時,他們將聖經翻譯成當地語言,為當地的非洲文化注入了新的解放性動力。新的信徒閱讀聖經時,他們獲得了工具,可以根據上帝的真理批判他們的傳統和文化,肯定其中真實和有效的部分,同時揭示其中不真實、因而對人有害的部分。因此,非洲的文化既得到了加強,還得到了改革,從而使基督徒能夠帶來真正的社會變革。
中國文化也是如此:基督教肯定了孝道和傳統家庭關係等價值觀。
最後,羅伯特·伍德伯裡(Robert Woodberry)在《自由民主的傳教根源》(The Missionary Roots of Liberal Democracy)一書中所做的研究證明,基督教在其紥根的所有國家與文化中,都促進了民主的成長與更好的政府。
因此,Cook和其他歷史學家能夠將焦點從帝國主義轉移到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建立的充滿活力的年輕教會。
第四部分:從1949 年至今,以及未來展望(1949 年至今)
14 沒有傳教士的土地:中國共產黨的崛起
這兩章追踪了王明道與宋尚節的生涯,將他們牢牢地置於二十世紀初中國思想和政治激盪的背景之中。
王明道接受過傳教士的教育,在傳教士教派中擁有光明的牧職前景。後來,他閱讀了最新的白話文聖經譯本後,他確信自己應當以信徒的身份接受浸禮。因此,他失去了西方宣教士的職位,並獨自創立了一個真正本土化的華人教會,透過講道和寫作,他成為全國知名的獨立華人教會領袖。
因此,他完全獨立於外國人,並非共産主義者和其他人指責基督徒的那種帝國主義的“走狗”。他提倡將聖經的原則應用在基督徒的生活和社會中,與那些依賴教育和政治行動來改革國家的現代主義者,以及認為可以透過革命改善社會的馬克思主義者截然不同。他抨擊社會中的罪惡,但他不參與政治和黨派活動。他堅持認爲,一個人必須“重生”才能經曆個人的改變,否則一切外部改革都隻是表麵的。
除了演講和寫作之外,他還組織基督徒成立教會,就像共產黨人組織他們推動革命一樣。他相信,藉由建立基督徒團體,轉化的信徒所產生的綜合影響力將會對社會造成衝擊。
當日本人佔領華北時,他拒絕加入政府控製的教會,就像他在共產黨掌權時所做的一樣。自始至終,儘管受到激烈的批評、巨大的壓力,最後更受到三自愛國運動領袖丁光訓(K. H. Ting)主教的逼迫,他仍然堅持獨立。結果,他(和他的妻子)在監獄中受苦多年。當他被釋放時,他幾乎雙目失明,身體殘缺不全,但他在靈性上卻是一位不屈不撓的領袖,深受中國未經註冊教會會員的敬佩。
Cook接著簡述了宋尚傑(John Sung)戲劇性的事蹟,他是一位激動人心、影響力極大的復興家和佈道家,儘管罹患可怕的癌症,他仍不屈不撓地在中國和東南亞各地宣揚福音。(我和Cook一樣,都覺得宋教仁作為基督徒領袖的魅力無窮。我唯一的疑問是,他的個人故事是否像某些人指控的那樣是虛構的)。
1949年之後,傳教士被迫離開,共產黨掌權並開始改變國家,中國基督徒必須適應沒有傳教士的生活。此外,強調「社會公義」的現代主義教會發現,政府有意介入並執行他們長久以來所倡議的一切,因此他們加入三自愛國運動,以適應這種新的情況。他們配合政府的政策,將整個社會統一在黨的控製之下。
另一方麵,「基要主義者」誓言要保持獨立,不受政府的控製,他們不會加入任何他們認為已偏離福音的「教會」。以王明道為一方,以丁光訓主教為另一方的兩派新教之間展開了激烈爭論。丁堅持認爲《羅馬書》14:1-2的意思是基督徒應該團結在一個旗幟下。然而,王明道反駁說,保羅指的是真正的基督徒,即相信聖經的人。現代主義否認聖經的主要真理,因此不應被視為基督裡的「弟兄」。基督徒應該拒絕尊敬這些人或與他們、以及支持他們的政府合作。
經過幾年激烈的爭論之後,王明道和其他與他誌同道合的人被關進監獄,這得到了丁光訓和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全力支持。那些與他們有相同信唸的信徒轉入地下,在家中聚會,並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麵對無情的迫害。他們似乎輸掉了這場戰爭,但Cook指出,他們展現了「驚人的堅持力」,他們後來以一個龐大的、靈性活潑且相信聖經的基督徒網絡出現。
15 沒有基督徒的國度:來自墳墓的勝利
「1950 年到 1990 年這段時期有兩個矛盾的現實,很難在一個簡短的章節中把它們並列呈現:一是這個國家遭受了一連串難以言喻的悲劇,二是教會奇妙地生存了下來,並在1980 年代的靈性復興中達到高峰」(181)。
首先,Cook 回顧了那段決定性年代眾所週知的歷史,包括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接著,他分享自己如何逐漸認識到 「神在那段艱難歲月中奇妙的作為」,最後以簡短的描述「甜美的敬拜和強烈的屬靈饑渴,成為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基要主義教會的特徵」(182)作結。「爺爺」成爲基督徒受苦和忍耐的一個例子。
家庭教會「以禱告、對上帝話語的熱愛、神跡奇事、溫暖的團契和快速的成長爲特徵」。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得以倖存,在基督徒與政府之間維持著脆弱的聯繫。
他在結論中指出了中國基督教如何「在全球基督教的更廣泛背景下展露頭角」。
16 走出黑暗的陰影,走向全球舞台的光明
在最後一章中,Cook 回顧了自 2000 年以來華人教會所發生的事,提出了“......可能會在未來幾代人的時間裡佔據中國基督徒思想家注意力的三個基本問題”,並分享了他 “在宣教運動中許多人的夢想,即一支強大的宣教力量將在中國興起”。
2003年以來
他認為,2003年是一個轉捩點。自 2000 年以來髮展起來的力量在新一輪的公開宣教中達到了頂峰。農村的復興仍在繼續,但是隨著基督徒大量湧入城市,城市裡受過教育的信徒成倍增加,他們的領袖在中華基督教中的地位也越來越突出,這導緻了向城市的大規模遷移。
Cook描述2003年一個感人的時刻:在一個關於中華向世界宣教的會議上,外國的基督徒宣教士被要求站起來,接受與會的2,000位中國信徒的認可。他們雷鳴般的掌聲表達了對前幾代傳教士所做一切的感激之情,他們的認可代表了他們已經準備好站起來,接過火炬並繼續前行。我當時也在那個會議上,感受到與他同樣的不配之感,同時也和他一樣感受到接力棒已經傳遞過去。同年在芝加哥也舉行了一場類似的聚會。
不過Cook指出,這些事件可能標誌著中華基督徒屬靈熱忱的頂峰。
三個問題
未來幾十年,中華基督徒可能會麵臨三個問題: 第一,“我們是誰?”
緊隨其後的兩個問題是:"華人信徒是基督徒優先,還是中國人優先?“我們的首要忠誠是什麼?” 就像今天的美國一樣,在中國,這種緊張關繫也可能導緻教會分裂。
第二:"我們與國家的關繫是什麼?
與這個問題相關的還有以下問題:
“基督徒應該在國家中扮演什麼角色?”
“他們應該在重大事件髮表意見,參與政治,支持革命,還是努力建設一個基督教國家?”
“我們與中華文化的關繫是什麼?”
“華人基督徒是否會試圖緩和這個國家正在崛起的帝國主義?”
最後 “基督教與中華文化的關繫是什麼?” “孔子與基督?” 在中國,一場激烈的辯論提出:"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中國社會之間的關繫是什麼,或者應該是什麼?” “中國神學家是否會''率先''在塑造中華文明的未來中髮揮突出作用?”
中華基督教的下一步是什麼?
Cook希望中華基督徒能夠與西方基督徒合作,成爲世界宣教的一支力量。這當然是可能的,甚至是很有可能的。他相信,上帝已經將他們從黑暗中帶入世界的光明之中,使他們成爲世界的光去服事。
評論:
《黎明前的黑暗》是一本重要著作。庫克非常巧妙地將文化背景和基督教曆史、大型運動和關鍵時刻、強大力量和傑出人物、他自己的經曆和他採訪過的華人的經曆編織在一起。Cook在主要神學院教授這一課程長達二十多年,包括以普通話授課的正道福音神學院(Logos Seminary)。他將課堂帶入書中,講述了他的中國學生如何回答有關敏感問題的提問。
Cook顯然希望這本書能成爲大學和神學院課程中有關中華基督教的標準教科書,我也希望它能實現這一目標。清晰的條理、簡潔的敘述、深思熟慮的學習問題、推薦閱讀和信息豐富的側欄,再加上作者頻繁地進入故事,所有這些結合在一起,使這本書成爲一個非常便於讀者和教師使用的工具。
必須將《黎明前的黑暗》與已故丹尼爾-貝斯(Daniel Bays)於2012年出版的同類著作《中華基督教新史》(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進行比較。這兩本書都聚焦於新教,但也提到了羅馬天主教,這是對讓-皮埃爾-夏博尼埃(Jean-Pierre Charbonnier)出色的調查報告(《中華的基督徒:公元600-2000年》,2002年出版)的認可,該報告主要關注羅馬天主教。貝斯對中華曆史上各個時期的主要人物做了更詳細的介紹,同時也沒有完全忽略每個時期的曆史背景。他對福音派大多持公平態度,但顯然更傾向於 “主流”、“普世 ”的基督教。
另一方麵,Cook從“堅定的福音派”視角進行冩作。他在每一章中都集中描冩了幾個關鍵人物,這些人物説明了更大的運動。最重要的是,Cook將中國基督教的故事完全置於中華曆史和文化背景之下。事實上,這種背景有時就像是故事中的 “主角”。此外,他顯然是在回應世俗曆史學家對傳教運動的批評。有時,他似乎在爲傳教士精心撰冩辯護詞。他對傳教士曆史的 “陰暗麵 ”始終保持着敏感,試圖對這些批評做出誠實的回答,並對傳教士的意圖,甚至是他們經常被誤解的行爲表示同情。
總體來説,我認爲《黎明前的黑暗》是對中華基督教研究的重大貢獻,也是對這一極爲重要的課題的重大學術處理。
作者:戴德理(G. Wright Doyle)
譯者:Elena Tao and Joseph Liu
爲了進一步閱讀,我建議以下“中华基督教研究”繫列中的書籍:《中國的城市基督徒》,作者佈倫特·富爾頓(Brent Fulton);《在國家中生存,重塑教會》,作者馬麗(Li Ma)和李进(Jin Li);以及《中國的注冊教會》,作者韋恩·滕·哈姆塞爾(Wayne Ten Harmsel)。我還推薦由我撰冩的兩本關於中华基督教書籍評論的合集:《中华基督教:文獻導論》和《中國的傳教運動:文獻導論》,可在此處找到。